近來把生活過得亂七八糟的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走一段很長的路把心裡的雜緒梳理清楚。但我離河太遠了,那走了三年的河堤,那閉著眼睛也能描繪的路線──總是夜晚,從萬壽橋頭木柵路端沿著階梯下去,順著平緩的斜坡來到河堤旁一個車道寬的步道。剛過九點,許多跑者全副武裝揮汗如雨,節制地控制呼吸一二、一二。後頭跟上幾個騎單車的人,多半是一家子牽著便宜的小折就出來的。父親挺著一顆大肚子騎在前頭吆喝,幾個幼兒與媽媽則是用自己的速度慢慢騎著,對爸爸過分的熱情理都不理。遛狗的人牽著狗繩,總是一臉疲憊與無奈,只剩那體型或大或小的毛孩帶著無窮盡的好奇東聞西嗅,最後再留下一筆印記宣示地盤。我總是沿著右側的堤道走,經過年輕人群聚的恆光橋底,接著順著河道蜿蜒向左再向右,過了一壽橋再是寶橋,若是跑步的話從這裡折返便莫約三十分鐘。回程的路上總是喘,風好像比來的時候更冷了一些,河在一旁靜靜流著好像疏懶又好像輕輕地搭理了什麼──只是,河離我太遠了。
房慧貞的《河流》便是以河為主題。她在年初的小塵埃寫了社會最底層的各色人物,是日光斜斜照進陰暗的房間才能目視的那些,筆鋒準確、冷靜。而她在《河流》裡頭仍然照見了過著低限生活的底層人物,並寫河的沖刷河的堆積彷彿聚落的拆散與遷徙;寫橋如何把人分隔成上層、下層的對立。她寫隱藏在夜市如河流的人龍裡,那些無人光顧的冷清攤販、風華褪去的流鶯,不須言詞的雞排店老闆;寫故鄉那些被時間刻蝕的老人如何堆著笑,像河流一樣收納時光帶來的誤解與差錯,靜靜聽著堤外河水聲聲唱。
她晶瑩的文字維持最低限度的動能,像一顆又一顆的空鏡頭,使筆下的眾生毫不矯飾呈現自然的狀態。至於那些人世間難以避免的苦難和痛楚,她也寫但仍然維持最節制的筆觸,不煽情不造作像從影片膠捲上輕輕剪下無關緊要的一格,但我們都知道無論之前之後都有事發生。她細細珍惜著這些時間的玻片,並像城市底下的水溝蟄伏在最底層收拾這城市的不能見人的秘密與掩飾。沒有關係的,她的文字不去判斷,水流慢下來的時候,距離出海口已經很近。
在2014年的第一天讀完這本書,我想起政大的河,想起那些在河岸邊像頹倒的傷犬讓河流撫慰的時光;我想起宜蘭河,想起一次颱風就把整個河岸邊的球場淹沒的景象;我也想起過去在課本上讀過關於台灣河流的描述:河短、坡度大、水流急,該留的留不住,比如文明、比如自尊、比如那些從視線角落閃過的佝僂身影、比如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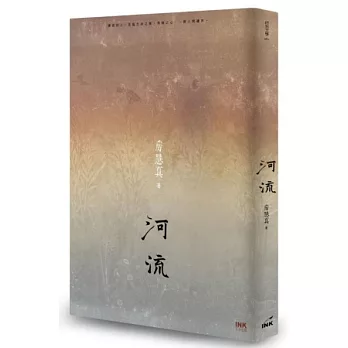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