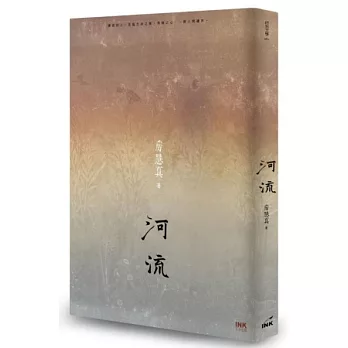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
《等》
在小車站等你
等你刺穿風景,像
一只折壞的紙飛機
卻擁有起飛的意圖
在很小的車站裡
等你,像河流等待雨季
河水淺淺的
輕輕淹過心跳的韻律
等待你
像鳥群乘著末班車的風
銜回築巢的枝梗
夕陽還在開展──
他們各自抵住這樣的風擦身而過
嗚咽的聲音像放遠的風箏細不可聞
2014年11月12日 星期三
【羊肉爐、蝴蝶麵,有時還有水餃】
昨晚和同事們一起吃飯,五個人圍著一鍋蔬菜羊肉爐。雖然一份鍋底的羊肉並不多,但用菜心和嫩薑為底熬煮而成的湯頭,有別於傳統藥膳羊肉爐的羶燥,仍然溫溫穩穩地讓身子從內而外暖起來。再夾幾口豆瓣醬拌薑絲炒成的羊肉,細細嚼來肉質鮮軟,應著輕輕叩門的冬日氣氛再合適不過。
飯後我們坐在位置上閒聊,偶爾還啜著熱湯捨不得放。這時一名同事問我:「你喜歡吃細細長長的義大利麵,還是扁扁的那種一顆一顆的義大利麵?」我聽了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喜歡一顆一顆那種,像是『啾啾』的形狀。」同事順著話題又問:「台灣是不是也有這種一片一片的啊,叫什麼名字......貓耳朵!貓耳朵!你也喜歡吃嗎?」我聽完以後點頭大力稱是,她又問了一題:「為什麼?」
「因為很方便吃啊。我喜歡吃那種一支湯匙就能解決的食物。」我篤定地說。
今天晚上,我冒著細雨將機車停在附近的水餃攤,點了十五顆水餃和一碗酸辣湯。這一攤的餃子雖然不算特大,但是切成細末的豬肉和著新鮮韭菜,吃來一點臊味也沒有。剛起鍋的水餃捱著彼此,熱騰騰地散著蒸氣。我頻頻對著水餃吹氣,除了能讓熱燙的餃子容易入口一些,也能讓餃皮變得緊實帶著彈牙的嚼勁。用筷子叉起一顆,蘸著店家自製的辣豆瓣醬,十五顆吃完也就這樣了結一餐。
吃飽飯後我撐著肚子,騎上機車時卻想起昨天一番無心的對談。我竟又選了一個方便吃的食物,很快、很飽,也算好吃,但我似乎很久沒有好好對待「吃」這檔事。即使是豐盛的公司團膳,也都只拿碗和一柄湯匙,避開需要剝殼挑刺的魚蝦蟹,菜汁肉汁裹著白飯,一口一口吞著,可實際上吞進什麼一到晚上就完全不記得了。
這幾乎是整個生活的隱喻啊,不是生活不深刻,只是吞得太快了,沒有細細品味紋理的餘裕。今天另一位同事對我說,有時候腦袋動得太快就容易對世界失去耐心。但在真正找到舒服的速度以前,把自己放在一個可以從容恣縱感官的位置是重要的。方便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新鮮刺激是一回事,深入且完整又是一回事。這是羊肉爐、蝴蝶麵以及韭菜水餃教會我的事。
飯後我們坐在位置上閒聊,偶爾還啜著熱湯捨不得放。這時一名同事問我:「你喜歡吃細細長長的義大利麵,還是扁扁的那種一顆一顆的義大利麵?」我聽了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喜歡一顆一顆那種,像是『啾啾』的形狀。」同事順著話題又問:「台灣是不是也有這種一片一片的啊,叫什麼名字......貓耳朵!貓耳朵!你也喜歡吃嗎?」我聽完以後點頭大力稱是,她又問了一題:「為什麼?」
「因為很方便吃啊。我喜歡吃那種一支湯匙就能解決的食物。」我篤定地說。
今天晚上,我冒著細雨將機車停在附近的水餃攤,點了十五顆水餃和一碗酸辣湯。這一攤的餃子雖然不算特大,但是切成細末的豬肉和著新鮮韭菜,吃來一點臊味也沒有。剛起鍋的水餃捱著彼此,熱騰騰地散著蒸氣。我頻頻對著水餃吹氣,除了能讓熱燙的餃子容易入口一些,也能讓餃皮變得緊實帶著彈牙的嚼勁。用筷子叉起一顆,蘸著店家自製的辣豆瓣醬,十五顆吃完也就這樣了結一餐。
吃飽飯後我撐著肚子,騎上機車時卻想起昨天一番無心的對談。我竟又選了一個方便吃的食物,很快、很飽,也算好吃,但我似乎很久沒有好好對待「吃」這檔事。即使是豐盛的公司團膳,也都只拿碗和一柄湯匙,避開需要剝殼挑刺的魚蝦蟹,菜汁肉汁裹著白飯,一口一口吞著,可實際上吞進什麼一到晚上就完全不記得了。
這幾乎是整個生活的隱喻啊,不是生活不深刻,只是吞得太快了,沒有細細品味紋理的餘裕。今天另一位同事對我說,有時候腦袋動得太快就容易對世界失去耐心。但在真正找到舒服的速度以前,把自己放在一個可以從容恣縱感官的位置是重要的。方便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新鮮刺激是一回事,深入且完整又是一回事。這是羊肉爐、蝴蝶麵以及韭菜水餃教會我的事。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四月末》
捻熄萌芽的念頭
不合時宜的雨,在四月
淹滿深不見底的樹洞
身體憶起那些破散的情狀
比如抝折的菸頭、唱爛的情歌
比如輕輕撥開熟透的瓜果
發現早已失去了種子
雨讓燈火都熄了
秘密全部溺死
有人還在等
我不忍說
不合時宜的雨,在四月
淹滿深不見底的樹洞
身體憶起那些破散的情狀
比如抝折的菸頭、唱爛的情歌
比如輕輕撥開熟透的瓜果
發現早已失去了種子
雨讓燈火都熄了
秘密全部溺死
有人還在等
我不忍說
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生》
畢竟也曾揣摩
並肩迎向晨光的那一刻──
黑暗自夢境裡消退
所有尚未了卻的心事
都泌出晶瑩的露水
是時候耕耘廢棄的田園
翻動荒蕪的僻壤
如果有風
是時候讓花粉散布
並打開塵封的窗
「風起
唯有努力生存」
如果有風
就緊緊握住彼此的手掌
------------------------------------
註:括號內字句引自法國詩人保羅‧瓦勒里(Paul Valery)的著作《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
並肩迎向晨光的那一刻──
黑暗自夢境裡消退
所有尚未了卻的心事
都泌出晶瑩的露水
是時候耕耘廢棄的田園
翻動荒蕪的僻壤
如果有風
是時候讓花粉散布
並打開塵封的窗
「風起
唯有努力生存」
如果有風
就緊緊握住彼此的手掌
------------------------------------
註:括號內字句引自法國詩人保羅‧瓦勒里(Paul Valery)的著作《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我們需要的是……》
世界很吵
還來不及收納春天
雨就從閃電間的縫隙
降落下來
總有一些極限
贅餘的時間在人群裡獨處
很多未來已經成為過往
我卻從來沒有真正越過什麼
靈魂濕濕的
有些時候我也想遠離
前往無雨的港灣
靜靜向遠方眺望
如果可以
就不小心看亂了星星
還來不及收納春天
雨就從閃電間的縫隙
降落下來
總有一些極限
贅餘的時間在人群裡獨處
很多未來已經成為過往
我卻從來沒有真正越過什麼
靈魂濕濕的
有些時候我也想遠離
前往無雨的港灣
靜靜向遠方眺望
如果可以
就不小心看亂了星星
2014年3月9日 星期日
【想念】
剛才出門買了消夜,也許是雨又或者是溫度,總之又突然讓我想起去年那些在雨中撐著傘的午夜漫步。那時的我偶爾和街邊的流浪貓相視對峙,其他時候我會走一段河堤,接著回來站在天橋上看著行車駛過,聆聽他們發出的聲音在住宅區裡頭反響轟轟。
我懷念那段日子。那些就算疼痛仍然把自己攤開,細細地觀賞每一道凹槽與紋理的日子。停下腳步,我在雨裡站立彷彿被陽光遺棄的行道樹,而漫著深棕色光害的木柵區還有人聲──我明白雨是不會停的,光是明白就已足夠。
當時的腦袋如同現在一般無時無刻不運轉,但我嫌它轉得太慢轉得不夠;而如今有的時候,只是有時候,我希望一切都能夠安靜下來,如同敲擊玻璃時那樣短暫、清脆的高音。如果某一天雨不下了,天空一片清澈,我能站在河堤的邊緣聽著水聲,在難得的寧靜裡放棄所有思緒,抬頭凝視夜空,直到眼睛睜得痛了就能看見星星。
我懷念那段日子。那些就算疼痛仍然把自己攤開,細細地觀賞每一道凹槽與紋理的日子。停下腳步,我在雨裡站立彷彿被陽光遺棄的行道樹,而漫著深棕色光害的木柵區還有人聲──我明白雨是不會停的,光是明白就已足夠。
當時的腦袋如同現在一般無時無刻不運轉,但我嫌它轉得太慢轉得不夠;而如今有的時候,只是有時候,我希望一切都能夠安靜下來,如同敲擊玻璃時那樣短暫、清脆的高音。如果某一天雨不下了,天空一片清澈,我能站在河堤的邊緣聽著水聲,在難得的寧靜裡放棄所有思緒,抬頭凝視夜空,直到眼睛睜得痛了就能看見星星。
2014年3月5日 星期三
《可以嗎》
可以嗎
迷路的時候就閉上眼
憑著直覺走
問也不問
真的可以嗎
疲憊的時候再打開一瓶酒
深深嗅聞水果死掉以後
腐爛的味道
如果愛你像從蛤蠣湯裡
挑出怎麼也打不開的那一顆
那麼賭氣把湯打翻 可以嗎
不然借我一隻鐵鎚 可以嗎
迷路的時候就閉上眼
憑著直覺走
問也不問
真的可以嗎
疲憊的時候再打開一瓶酒
深深嗅聞水果死掉以後
腐爛的味道
如果愛你像從蛤蠣湯裡
挑出怎麼也打不開的那一顆
那麼賭氣把湯打翻 可以嗎
不然借我一隻鐵鎚 可以嗎
2014年3月1日 星期六
【0301自由書寫】
凝視的錯誤
是崖上吐信的蛇
一分為二
還是敵不過一把銳利的剪刀
手的酸楚只因為寫出太平凡的字
我不能回頭檢視
絞碎的初衷
也不能停止補充
答非所問
位於存在與虛無中間
呼吸道也長了軟軟的刺
而臉上的痣說不定
也有衝動變得有害一些
如果不夠漂亮可以嗎
如果成為眾人之城可以嗎
如果寫下擦不掉的問號可以嗎
詩是點燃引擎的車
你是比跑道更平整的意義
是崖上吐信的蛇
一分為二
還是敵不過一把銳利的剪刀
手的酸楚只因為寫出太平凡的字
我不能回頭檢視
絞碎的初衷
也不能停止補充
答非所問
位於存在與虛無中間
呼吸道也長了軟軟的刺
而臉上的痣說不定
也有衝動變得有害一些
如果不夠漂亮可以嗎
如果成為眾人之城可以嗎
如果寫下擦不掉的問號可以嗎
詩是點燃引擎的車
你是比跑道更平整的意義
【0228自由書寫】
思緒是一顆顆的葡萄
假象是古井裡雜草叢生
我揪出固著的針頭
並且拒絕欣羨你的來處
為什麼我挑選並且談論
很多的恢復;很多的進展
以及裡裡外外翻過來便可再穿的
兩面式設計
我們都是鵝也是薑母鴨
雨後踩破水窪的根部
其實我也有鯨魚般的企圖
痛是生產與分娩的
以及最後剪斷臍帶;
期待是一座生生不息的火爐
在暗夜裡照得我比誰都清楚
假象是古井裡雜草叢生
我揪出固著的針頭
並且拒絕欣羨你的來處
為什麼我挑選並且談論
很多的恢復;很多的進展
以及裡裡外外翻過來便可再穿的
兩面式設計
我們都是鵝也是薑母鴨
雨後踩破水窪的根部
其實我也有鯨魚般的企圖
痛是生產與分娩的
以及最後剪斷臍帶;
期待是一座生生不息的火爐
在暗夜裡照得我比誰都清楚
【0224自由書寫】
時間是窄的
我吹散槍口的煙硝
瞄準高尚的念頭
未曾出過任何差池
匱乏成了常態
我們像衛生紙般蜷縮
並溶解在寂寞的酸液裡
發出持續的底噪
我的睡意是一管捲好的菸
那些沉澱的
另外擇期追悼
直到需要點名的時候
才要他們立正站好
我吹散槍口的煙硝
瞄準高尚的念頭
未曾出過任何差池
匱乏成了常態
我們像衛生紙般蜷縮
並溶解在寂寞的酸液裡
發出持續的底噪
我的睡意是一管捲好的菸
那些沉澱的
另外擇期追悼
直到需要點名的時候
才要他們立正站好
【0223自由書寫】
山谷的邊際不留標記
流淌一段橙色的氣味
而你在彼端用天線接收
那如蜜般濃稠的
字的賀爾蒙
用三公分的步伐
淺淺的不濺起任何水花
並不修剪,只是堤防
當夢想氧化成一句髒話
害怕清洗自己
會令我丟失疼痛的憑據
如果路分歧開來
最後誰也沒跟上
只剩風讓風箏飛
讓火更猖狂
而洪荒起初就是你的光亮
流淌一段橙色的氣味
而你在彼端用天線接收
那如蜜般濃稠的
字的賀爾蒙
用三公分的步伐
淺淺的不濺起任何水花
並不修剪,只是堤防
當夢想氧化成一句髒話
害怕清洗自己
會令我丟失疼痛的憑據
如果路分歧開來
最後誰也沒跟上
只剩風讓風箏飛
讓火更猖狂
而洪荒起初就是你的光亮
2014年2月22日 星期六
【0222自由書寫】
一切的變更都來自捨與求
狡猾的剪影終究裂了把戲
低空的煙火點亮山頭的肩膀
明亮且銳利
我曾是輝煌的顏色
是舢舨上的渡船人
是退縮在岬角的鯨魚
不善說謊
只是淡淡地流瀉
周而復始
憤怒是不能僥倖的結晶
用左手寫左邊才能唱的歌
反正你也不曾用花奉獻給蝴蝶
我又何必;我又何必。
狡猾的剪影終究裂了把戲
低空的煙火點亮山頭的肩膀
明亮且銳利
我曾是輝煌的顏色
是舢舨上的渡船人
是退縮在岬角的鯨魚
不善說謊
只是淡淡地流瀉
周而復始
憤怒是不能僥倖的結晶
用左手寫左邊才能唱的歌
反正你也不曾用花奉獻給蝴蝶
我又何必;我又何必。
2014年2月16日 星期日
【0216自由書寫】
強大是一場實境秀
那些趕不上的字
是被矯正的靈感
意義則是最終極的完結
價值總令我失憶
一隻尋父的魚忍受著像山一般的刺
坡道上有人走來
談論著詩如何成為維持表象的方式
少一點缺乏
少一點毛毛的秒針
少一點潤絲精的困境
才讓生活冒油並且滑順
那些趕不上的字
是被矯正的靈感
意義則是最終極的完結
價值總令我失憶
一隻尋父的魚忍受著像山一般的刺
坡道上有人走來
談論著詩如何成為維持表象的方式
少一點缺乏
少一點毛毛的秒針
少一點潤絲精的困境
才讓生活冒油並且滑順
2014年2月11日 星期二
《早晨過後》
早晨過後
只剩下灰濛的天色
車輛駛過凹陷的路面
濺起陣陣水花,像眼淚
我不忍聽
行駛的列車
在地底像缺氧的水缸
每一天我被吞食
被吐出
重新消化一次
未經誰的允許
雨卻依舊下著
在傘面上發出三拍子的聲音:
崩塌塌、崩塌塌──
時間是比較大的齒輪沿著心頭的缺口輾壓過去
只剩下灰濛的天色
車輛駛過凹陷的路面
濺起陣陣水花,像眼淚
我不忍聽
行駛的列車
在地底像缺氧的水缸
每一天我被吞食
被吐出
重新消化一次
未經誰的允許
雨卻依舊下著
在傘面上發出三拍子的聲音:
崩塌塌、崩塌塌──
時間是比較大的齒輪沿著心頭的缺口輾壓過去
2014年2月9日 星期日
《夕陽照得我們都美麗起來》
日子像個方正的盒子
每一天我靜靜累積
並且反覆傾倒
尖銳的碎片;
而你像是青苔輕輕攀上內側
潮濕的念頭就讓你整面蓬勃生長
念頭就這麼深
沿路上我努力揀選
走累的時候我也丟棄一些
假裝自己還是輕盈的樣子
有時候也會開始擔心什麼也沒有了
便訂妥一套來回車票
換上扁平的臉孔
喝烈酒、抽便宜的菸
閉著眼睛聆聽列車上
陌生人的靈魂碰撞
發出鏗鏗鏘鏘的聲音
寂寞還在起浪
心底的海將無人聞問的全部收拾
沙灘上的空殼缺少誰寄居的痕跡
海風將你的衣襟吹起
你輕輕哼唱著歌
夕陽就照得我們都美麗起來
每一天我靜靜累積
並且反覆傾倒
尖銳的碎片;
而你像是青苔輕輕攀上內側
潮濕的念頭就讓你整面蓬勃生長
念頭就這麼深
沿路上我努力揀選
走累的時候我也丟棄一些
假裝自己還是輕盈的樣子
有時候也會開始擔心什麼也沒有了
便訂妥一套來回車票
換上扁平的臉孔
喝烈酒、抽便宜的菸
閉著眼睛聆聽列車上
陌生人的靈魂碰撞
發出鏗鏗鏘鏘的聲音
寂寞還在起浪
心底的海將無人聞問的全部收拾
沙灘上的空殼缺少誰寄居的痕跡
海風將你的衣襟吹起
你輕輕哼唱著歌
夕陽就照得我們都美麗起來
2014年1月28日 星期二
《失物》
曾幾何時
我是個溫柔的人
緩慢地駕車
不開窗,聆聽指示
揣摩曲折的意圖
偶爾還有良善的時候
比如撿起一只
無主的失物
並在原地靜靜地等
定時在夜裡哭
也不打算寫完那封未遞的信
只把愛從生活裡篩出
剩餘的便無所謂讓誰領回
我是個溫柔的人
緩慢地駕車
不開窗,聆聽指示
揣摩曲折的意圖
偶爾還有良善的時候
比如撿起一只
無主的失物
並在原地靜靜地等
定時在夜裡哭
也不打算寫完那封未遞的信
只把愛從生活裡篩出
剩餘的便無所謂讓誰領回
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
【在那之後】
他在林地裡隱隱按著右邊破舊長褲的口袋像保護著什麼。
他想起數年前他還意氣風發地數落著那些戴著疲倦面孔的人,他嘲笑這座島像一片巨大的順向坡,只要第一聲砲火響鳴就會整座坍塌。人生就是戰爭,他之所以一直這麼相信著是因為他認為他一定會戰勝,不然怎麼能不怕呢?每一把刀每一支槍,每一個連通身前與身後的巨大傷口。
只是沒想到會是這樣結束的,一場所有人似乎都有預感的爆炸。靠近一點的人全死了,而那些不上不下的便吞了政府的指令,抱持著還能好好活著的信念,分兩路沿著東西的海岸線各自撤退。路是這麼的塞啊,像這座城慣有的過敏性鼻炎。蜿蜒的山像巨大的停車場,耐不住的人便下來徒步走著。那些幸運沒被炸死的達官顯貴全坐了最快的飛機離開這裡,該說一切空轉嗎?卻又似乎沒有什麼區別,人們還是笑還是哭,還是在道路上席地而坐,在黑暗裡編造著長壽劇還沒演完的故事。樂天的性格不只使他們在危險來臨前毫無意識,還讓這些倖存者在悲劇發生後繼續無動於衷。
這是第二天。他站在高處往那座盆地望,一片漆黑像是座深不見底的湖,他抬頭看,看不見星星。他從人群裡逃開,散發不去的水氣讓他隱隱作嘔,果然該來的還是要來的嗎?他有種不祥的預感。其實只要再走一段路或許他就能獲救──啊,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畢竟還是台灣人,在最後一刻仍然抱持最難以動撼的天真。
雨水下來的時候,他終於放下抵抗。他拿出口袋裡的物事──是他逃難時匆匆忙忙撕下來的詩句。沾滿灰塵的雨水漸漸把字穿透,是他最愛的一首詩寫著雨水如何打進眼睛。他想起故鄉的雨滴總在窗邊敲擊一聲一聲,而在雨水燒起來以前,他暗暗在心底祈禱這世間還有人能夠記住他的名字。
2014年1月1日 星期三
【河流】
近來把生活過得亂七八糟的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走一段很長的路把心裡的雜緒梳理清楚。但我離河太遠了,那走了三年的河堤,那閉著眼睛也能描繪的路線──總是夜晚,從萬壽橋頭木柵路端沿著階梯下去,順著平緩的斜坡來到河堤旁一個車道寬的步道。剛過九點,許多跑者全副武裝揮汗如雨,節制地控制呼吸一二、一二。後頭跟上幾個騎單車的人,多半是一家子牽著便宜的小折就出來的。父親挺著一顆大肚子騎在前頭吆喝,幾個幼兒與媽媽則是用自己的速度慢慢騎著,對爸爸過分的熱情理都不理。遛狗的人牽著狗繩,總是一臉疲憊與無奈,只剩那體型或大或小的毛孩帶著無窮盡的好奇東聞西嗅,最後再留下一筆印記宣示地盤。我總是沿著右側的堤道走,經過年輕人群聚的恆光橋底,接著順著河道蜿蜒向左再向右,過了一壽橋再是寶橋,若是跑步的話從這裡折返便莫約三十分鐘。回程的路上總是喘,風好像比來的時候更冷了一些,河在一旁靜靜流著好像疏懶又好像輕輕地搭理了什麼──只是,河離我太遠了。
房慧貞的《河流》便是以河為主題。她在年初的小塵埃寫了社會最底層的各色人物,是日光斜斜照進陰暗的房間才能目視的那些,筆鋒準確、冷靜。而她在《河流》裡頭仍然照見了過著低限生活的底層人物,並寫河的沖刷河的堆積彷彿聚落的拆散與遷徙;寫橋如何把人分隔成上層、下層的對立。她寫隱藏在夜市如河流的人龍裡,那些無人光顧的冷清攤販、風華褪去的流鶯,不須言詞的雞排店老闆;寫故鄉那些被時間刻蝕的老人如何堆著笑,像河流一樣收納時光帶來的誤解與差錯,靜靜聽著堤外河水聲聲唱。
她晶瑩的文字維持最低限度的動能,像一顆又一顆的空鏡頭,使筆下的眾生毫不矯飾呈現自然的狀態。至於那些人世間難以避免的苦難和痛楚,她也寫但仍然維持最節制的筆觸,不煽情不造作像從影片膠捲上輕輕剪下無關緊要的一格,但我們都知道無論之前之後都有事發生。她細細珍惜著這些時間的玻片,並像城市底下的水溝蟄伏在最底層收拾這城市的不能見人的秘密與掩飾。沒有關係的,她的文字不去判斷,水流慢下來的時候,距離出海口已經很近。
在2014年的第一天讀完這本書,我想起政大的河,想起那些在河岸邊像頹倒的傷犬讓河流撫慰的時光;我想起宜蘭河,想起一次颱風就把整個河岸邊的球場淹沒的景象;我也想起過去在課本上讀過關於台灣河流的描述:河短、坡度大、水流急,該留的留不住,比如文明、比如自尊、比如那些從視線角落閃過的佝僂身影、比如愛。
【2014】
一個年過去了我卻沒有感覺自己重新開始。
每一天我走過日夜的交界,重複著對時間的迷信:所謂明天會更好、週五就要來到,比如「新的一年我決定要重新開始」。錯了。那些來自過去的,好的壞的,都會反覆像胎記、像紋身,像熱燙燙的生命在身體上烙下的疤痕,我明白的,我早已不是一個乾淨的人。
時間像一條長河從上游沖刷細小的砂粒下來,只有那些輕巧的才能到達遠方,並且在時光緩慢的時候漸漸沉積下來,出海口一道大浪打來就有人就被沖散,至於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我們不必等著誰回來就已經是失落沙洲。
關於年與年之間的跨越、轉變,以及所有悲傷或讚揚的隱喻都是假的,除了1314一生一世。這很公平。這是我們都擁有並正在盡情揮霍的物事,沒有誰真的可以勝過彼此。
每一天我走過日夜的交界,重複著對時間的迷信:所謂明天會更好、週五就要來到,比如「新的一年我決定要重新開始」。錯了。那些來自過去的,好的壞的,都會反覆像胎記、像紋身,像熱燙燙的生命在身體上烙下的疤痕,我明白的,我早已不是一個乾淨的人。
時間像一條長河從上游沖刷細小的砂粒下來,只有那些輕巧的才能到達遠方,並且在時光緩慢的時候漸漸沉積下來,出海口一道大浪打來就有人就被沖散,至於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我們不必等著誰回來就已經是失落沙洲。
關於年與年之間的跨越、轉變,以及所有悲傷或讚揚的隱喻都是假的,除了1314一生一世。這很公平。這是我們都擁有並正在盡情揮霍的物事,沒有誰真的可以勝過彼此。
訂閱:
意見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