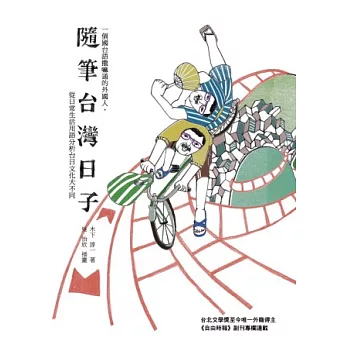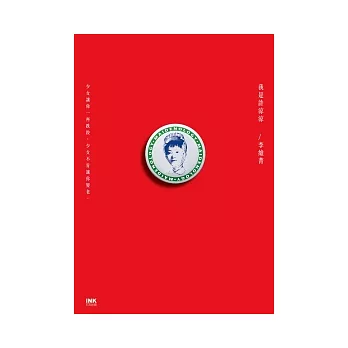雨的反面不是晴天
夢的反面不是清醒
山裡的村莊慶祝久旱甘霖
坡邊泥流也滾滾而下
如果濕潤的樹林燃起森林大火
如果高聳的城牆傾倒頹圮
如果月台上你邁步狂奔
沒趕上夜裡整點的末班車
是火車走得太早還是
你,來得太晚
你恨世界自顧自地走了
你沒聽見陣陣風起蟬鳴
得到的反面不是失去
小心翼翼的右手舉起鏡子裡的左手
手心刻著相同的命運:
有人把鏡子打破 留下其中之一
有人對鏡子笑了 和自己握手言和
你的視線從不客套
像箭穿過 像長矛戳破潰瘍的傷口
像雨淋濕白色外衣
透漏侷促的羞恥:
比如牙醫診所裡張開蛀牙的嘴
同時支吾辯護
「我平時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曾經善良 相信命運
我們模仿僵持不下的貓
以視線鏖戰
直到過去的詩比現在的好
我當不成詩人也不是愛人
你太好 總是不忍告訴我
溫柔讓思緒如皮屑般散落
在世界開始厭煩以前
只是看 你只是看
像箭穿過 像長矛戳破潰瘍的傷口
像雨淋濕白色外衣
透漏侷促的羞恥:
比如牙醫診所裡張開蛀牙的嘴
同時支吾辯護
「我平時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曾經善良 相信命運
我們模仿僵持不下的貓
以視線鏖戰
直到過去的詩比現在的好
我當不成詩人也不是愛人
你太好 總是不忍告訴我
溫柔讓思緒如皮屑般散落
在世界開始厭煩以前
只是看 你只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