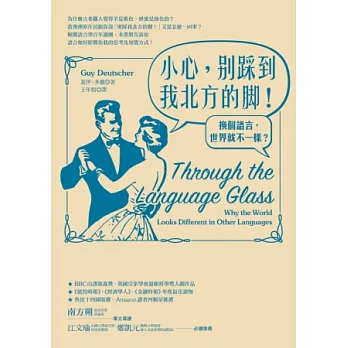「從我告訴你的那天開始。」他的聲音穿過雨滴,字字清楚地傳到我的耳裡。雨下得好大,都從窗戶的縫隙潑進來了。我站起來走到窗台邊,把窗子緊緊關上,氣密窗把雨聲和水氣都隔絕在病房外面。好安靜。幾乎都能聽見空調和我們的呼吸隱隱共鳴的聲音。
我看向窗外,雨水拍打著醫院大門植栽的樹葉,馬路對面幾個學生把書包頂在頭上跑過,淋得全身濕透。他沒繼續說話。怎麼了?我回過頭去。他的雙眼直向著病床對面的白牆,目光卻像穿透了牆的本質而看見了更深遠的,躲在牆背後的東西。
那是回憶的表情。他曾說過因為這種病,使他在腦海重新找回記憶的時候,必須比平常加倍專注。
「不然的話,會讓回憶和現實重疊。我曾經失敗一次,我只能說……空間失序已經夠糟了,而混亂的時間更加可怕。」他嘆了口氣,一反平常嘻皮笑臉的模樣。我和他捧著早已喝完的空咖啡杯,並肩坐在校園側門附近的長椅上。冷風狠狠地吹,天色卻越來越明亮。那一場大雨終究是被烏雲忍著沒下來。
「病況沒辦法改善嗎?」我蹙著眉頭問。
「目前是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辦法,但我好像已經找到和『他』共處的方法了。」他笑了,雙眼彎著像貓。「在我的世界改變之前,會有一些徵兆。一開始是視線的角落出現異常,比如顏色突然閃了一下,或者是物體突然縮小或膨脹,而下一個階段就是視線的中央……」他轉過來看著我,指了指他深灰色的虹膜,「正中間的地方,會像漣漪般一圈圈向外擴散、變形,如果真的到了這個階段就慘了。」
我看著他的側臉,像孩子一樣的天真神情。明明應該是很悲傷的事。
「醫生建議我在這個階段閉上眼睛,安安靜靜休息,等著症狀過去。只是有時候我人在外面,不可能隨時都找得到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後來我自己找到一個方法。」他揚起右手,上頭戴著一只金屬錶帶的指針式手錶。「電子錶不行喔,發病的時候必須要像這樣盯著秒針看,嘴裡跟著它數:『一秒、兩秒、三秒……』回過神來,症狀就解除了。」
我在腦裡搜索著幾個比較恰當的回應,嘴巴卻幾乎是反射性地冷冷淡淡回了:「是嗎?」
「那天是我第一次在夢裡發病。」他像是沒聽見我的回答,自顧自地繼續說著,「那是醫生最擔心的狀況。他說如果哪一天我在夢裡發病,可能就是病情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沒有辦法控制?」我害怕讓他誤會,小心翼翼地問,「意思是,假的世界會漸漸……取代真實世界?」
他開朗地笑了幾聲。烏雲已經完全散了,冬日淡淡的夕陽像漲起的潮水,從天邊輕輕湧上來。
「誰知道呢?」他轉過頭來看著我,視線透徹穿過我的雙眼。「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你是除了我的家人和醫生以外,第一個知道的人。」
為什麼呢?我站在窗台邊,靜靜等著他從記憶裡回航。為什麼,對我說呢?這是我這些年來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問。
那天傍晚,我們還是像平常一樣道別,他迎向陽光的背影看起來很模糊。走回宿舍的路上我不斷揣摩,所謂想像出來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呢?一段階梯在他眼裡可能是一道瀑布,宿舍的門也許是通往秘境的山洞,而成群飛過的燕鳥就成了一張巨大風箏。那我呢?打開寢室房門的時候,我像被雷殛般突然想起:「那我呢?」
那晚,我把他從牆邊拉下來的時候,即使只是一個瞬間,他的確是清清楚楚地看見了我。那麼,我在他的幻境裡是什麼模樣呢?
「我看不見咖啡上的奶泡。」他幽幽地說,他回來了。「當我喝著那杯咖啡的時候,我的上唇感受得到奶泡的細微觸感,舌頭也嚐到了肉桂粉的辛辣味道,可是我看不見。就像有人拿了橡皮擦謹慎擦去一般,那一層奶泡徹底消失了;杯子裡面是普通的拿鐵咖啡,沒有奶泡的拿鐵咖啡。」
我感覺我自己憋著一口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終於如我所願的,沒有新的世界。在我們……不再見面以後,舊的世界加速地被那個擦去奶泡的橡皮擦,毫無遺漏地擦得一乾二淨。」他深吸一口氣,接著緩緩吐出。「什麼都沒有了。就算我聽得到、嗅得到、摸得到、嚐得到,我卻連我自己都看不見。我的世界只剩一片空白,什麼都沒有了。」
好安靜。
突然,他轉過頭來,目光像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山路裡,兩盞在蜿蜒道路上忽明忽滅的車燈。
「但我看得見你。」他說。窗外的雨下得更加猛烈了,但病房裡卻一點聲音也聽不見。「我看得見你。」